我提早踏进了办公室,希望在第一个病人驾临之前仍有片刻的安静,这是我一向的习惯。我瞄了一下这个依旧在幽暗中的房间&mdash&mdash书桌、舒适的椅子、以及坐落在窗前的黄颜色的沙发,我深深的感觉到,从事精神病医学的行业确实是令人相当满足的。我已经干了十三年的医生,这些年间,我常在意识中认为,自己所治疗的只是病人的某些部分而已,充其量只是在诊治疾病所显出来的征兆,而绝非在对付疾病。我在维金尼亚州利趣门的纪念医院工作,这里向其他规模宏大的现代医院一样,没有时间让我把病人当作&ldquo人&rdquo来了解,也没有时间让我倾听病人在诊断室所发的问题背后,那些真正的问题。因此,在四十岁时,我又回到了学校。这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我必须要求妻子离开利趣门而搬往沙罗特维,并将两个孩子迁出学校,同时放弃自己在利趣门医士训练学院的院长职位而住进学校宿舍读上几年的书。然而自决定至今的十二个年头里,我多次因这抉择而感觉欢悦,并且今天在这一日之始的安静时刻中,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欣喜。我轻轻弹开桌面上挂号用的活页夹,按顺序看着今天约诊的名单:密特莉、姜彼得、珍马汀,随即我的指头停了下来。(注一:病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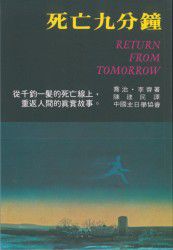
评论共0条